来源公众号:教育学人AIED 作者:李小祖逸
我们曾介绍过,美国课程重构中心的方法论研究《The Power of Proofs (Much) Beyond RCTs》探讨了当前教育研究领域对”随机对照试验“的误区,讨论为何教育研究“供不应求”或“供而无效”,以及应如何改进研究方法与知识生产模式才能更好满足教育实践需求(见:教育研究方法论:什么样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今天我们借比斯塔在2007年的研究《WHY “WHAT WORKS” WON’T WORK》再次讲讲这个话题。教育界流行把教学变成“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仿照医学用“随机对照试验”等来判定“what works”。Biesta 认为这种做法在教育领域造成一种“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
当“有效性/效率”变成唯一判准,教育决策被收缩为技术问题,谁来决定“该往哪儿有效”(目的、价值)的空间被压缩,参与者(教师、学生、家长、公民)的话语权被削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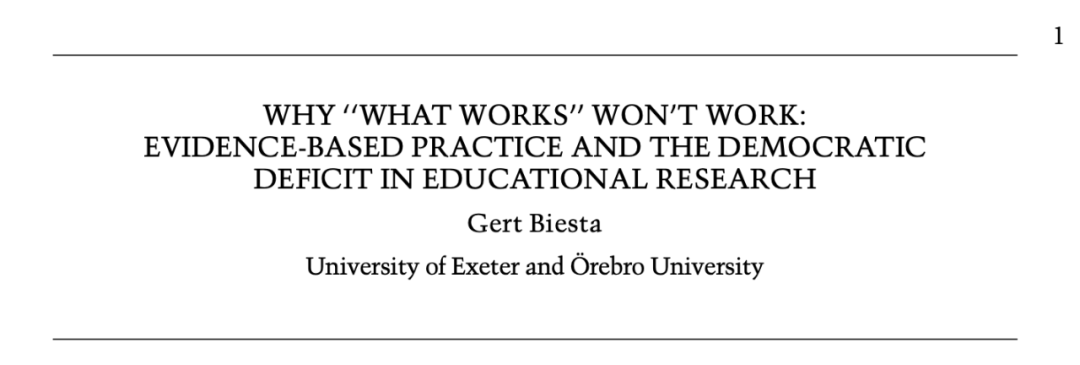
一、为什么“实证研究”风靡教育界(西方)
1999 年英国的 Excellence in Research on Schools Report 批评教育研究与政策脱节、缺乏清晰证据。英国由政府与督导机构对教育研究“质量/相关性”的质疑,引出系统综述、实证汇编、教师“找什么最有效”的网络与研究议程的集中化;OFSTED、EPPI-Centre(证据库)等机构推动建立教师易于使用的“what works”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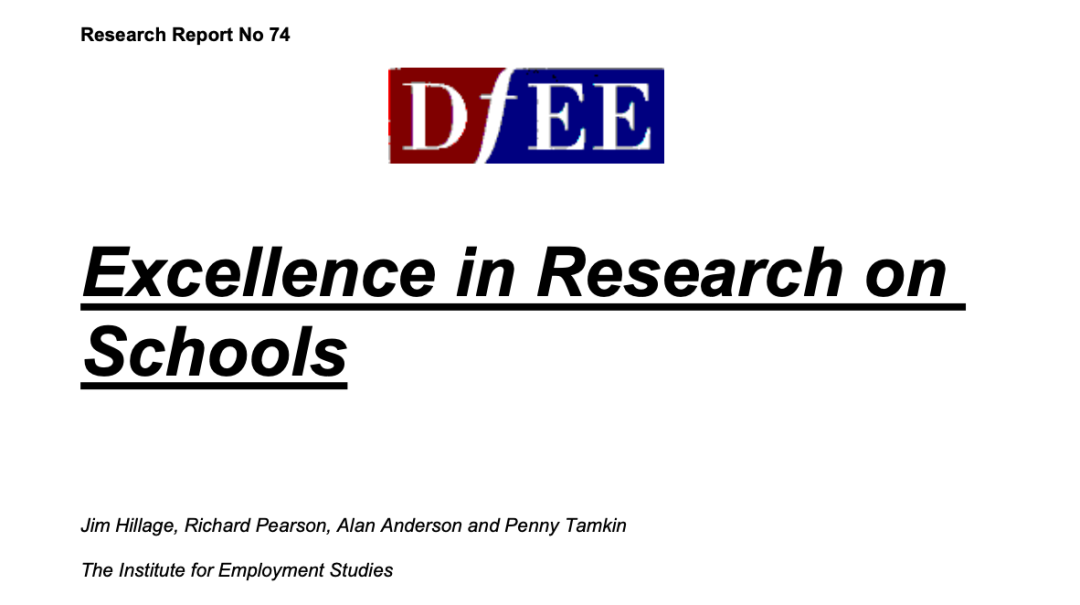
2002 年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提出 “scientifically based research”,强化RCT(随机对照实验)为金标准。在“NCLB”后更把RCT奉为金标准。政策主张教育研究应该像医学、农业、工程一样为实践“提供可直接应用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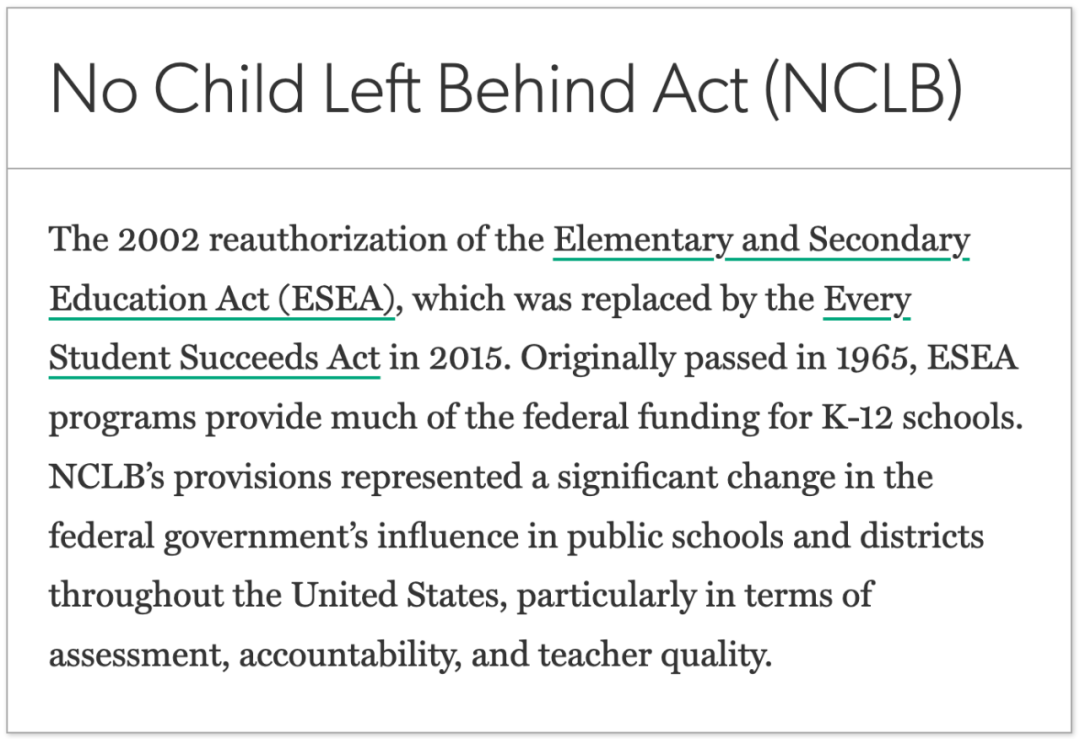
当然这个潮流的推行也不是一马平川,也有很多针对这些动向的抵制声音:
…教育不是工程学,不是用科学就能确定“正确方法”的事情……实证主义思维(positivism)、管理主义和“研究专家中心主义”削弱教师专业性…
这些质疑都很合理,但比斯塔希望进一步,他发现很少人从根本上质疑:“教育是否适合‘what works’的逻辑?”于是Biesta 在此提出:我们要追问的不是“如何更好地用证据”,而是“何种证据与何种判断适用于教育?”这继承了杜威的实践认识论(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Pragmatist View):
杜威认为,研究不是告诉你做什么,而是帮助你判断该怎么做。
所谓“知识”不是确定的规则,而是让我们在不确定情境中更智慧地行动的工具(warranted assertibility)。
因此,研究提供“what worked”(过去),而不是“what works”(现在或未来)。
Biesta 在这里重申教师的重要性:
教师不是“执行已有证据的技术工人”,而是要在具体情境中综合证据、价值、经验、处境做判断。
“教育实践中该做什么”不能由数据决定,而必须由专业与公共讨论决定。
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证据”很快就会变成一种技术官僚的主宰工具。
二、教育是有意义的交流
(Education as Meaningful Communication)
比斯塔回顾了“循证教育”的四个核心前提:
1)教学行为是干预行为(intervention),能导致可预测的结果。
2)教育研究的任务是识别“什么干预对谁有效”。
3)实验设计(RCT)是评估干预效果的最佳方法。
4)教师应遵循已被证明“有效”的方法。
比斯塔认为,这种逻辑等于把教育当作一种中性技术过程(value-free technical process),但教育从来都是价值驱动的社会实践(value-laden social practice)Biesta 在这一节展开哲学反击:
1)教育不是简单因果链,而是有意义的交互(meaningful interaction)。教育不是这种单向的因果传递,而是充满不确定性、解释性与互动性的过程。
举例:同一句话“你真聪明”在不同文化、语气、场合下可以被解释为表扬、讽刺或嘲弄。
2)教师的“干预”只能创造可能性结构,不能保证结果。
3)教学中学习者拥有回应自由、解释自由——这是教育“主体性”的根本。学习不是教师“灌输”的结果,而是学生在特定情境中主动回应和解释外部刺激的过程。
4)所谓“效果”也并不来自教师的干预行为本身,而是复杂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生成的。
Biesta 提出,教育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有意义的交流(meaningful communication),用“干预—效果”的医学模型套用教育,是本体论上的错误。Biesta 在这里隐含了哲学立场的转向:
如果教育是一个规范性(价值导向)且意义生成的过程,那么,“what works”逻辑就必须退居从属地位。
“what works”假设我们已有明确的目标,只需找出最好的手段。
但教育的问题常常是目标本身就尚未达成共识。
例如:我们是要培养“乖孩子”还是“批判性思维的公民”?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价值判断!
因此,教育必须保留对“目标何在”的开放性讨论,不能只谈“手段有效性”。就比如前几天我们讲过的,很多学校开展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可是开展这个课程的目的何在?大多数实践都没有把目的搞清楚(培养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是什么?)。
作者在文末强调,如果我们继续让“evidence-based practice”(循证实践)成为教育研究的主导模式,并且默认其所采用的“干预—效果”逻辑,我们会产生严重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会限制研究与教师的能动性,也会剥夺公众(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公民)对于“教育目的”的讨论权。
三、比斯塔对后续教育研究范式的影响
论文把“what works”框架中的民主赤字与价值盲点说清楚后,成为后续综述中引用的规范性批评代表作之一;许多综述在讨论反对证据本位(EBE)时都会直接点名 Biesta(2007、2010)并据此强调教育是价值驱动、而非单纯“效果最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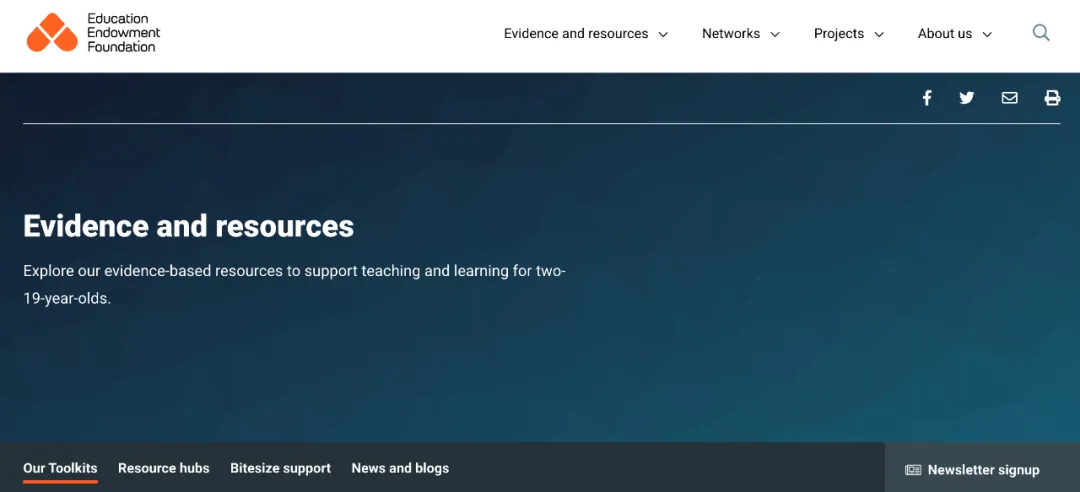
英国 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EEF) 的指导材料近年来持续强调:证据要与学校情境、实施流程、专业判断结合,用“结构化但灵活”的实施循环来落地证据—而不是把证据当成即取即用的“处方”。这种实施导向、情境敏感的路线,与 Biesta 强调研究应启发判断而非取代判断的立场同向。
同时,英国将 EEF 定位为“证据守护者”、建设研究学校网络等制度性安排,标志着从单纯追求“金标准实验”转向证据生产 + 证据使用双轮驱动,并在材料中反复使用“evidence-informed / evidence-influenced / evidence-aware”的措辞,试图改变evidence-based的广泛应用。
通过后续影响来看,它没有反对实证,但改变了证据被使用的方式与话语——推动教育界从“基于证据”(evidence-based)走向“证据指导+ 专业判断 + 情境实施”(evidence-informed),并在政策、机构与研究方法上留下了清晰的折射。
参考文献:Biesta, G. (2007). Why “what works” won’t work: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the democratic deficit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Educational theory, 57(1), 1-22.



 扫码安装网站APP(Android版)
扫码安装网站APP(Android版)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