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众号:安东之子 作者:杨先武
自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颁布以来,语文教坛出现了一些冠之以“大”的新概念,最引人关注的非“大单元”莫属。只要翻开教学刊物,就会发现大单元教学已成热门话题。但时至今日,大单元教学究竟怎样实施,没有人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广大一线教师对大单元教学多持观望甚至排斥的态度,鲜有积极践行者。笔者认为,这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教育观念滞后,而是因为“大单元”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模糊概念,大单元教学的推行存在脱离实际的盲目性,致使这一“探索”陷入了困境。
一、如何理解“探索大单元教学”?
前不久,有位明确表示不认同大单元教学的著名特级教师在一次视频讲话中谈到:“2022年版的新课标有5万多字,你查询‘大单元’三个字。没有!没有,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了!”应该说该教师“不用去管它”的态度无可指责,但其理由并不那么充分。只要有利于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即便是课程标准中“没有”的,同样可以大胆探索,例如“三主四式”“语感教学”“情境教学”“点拨法”等都是课程标准(过去称教学大纲)中没有的,不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吗?还要知道,虽然修订后的语文课程标准没有出现“大单元”三个字,但对于各科教学都具有指导意义的课程方案(2022年版)已在课程实施中提出了“探索大单元教学”,这正是某些人极力推行大单元教学的重要依据。因此,问题不在于课程标准中有没有“大单元”三个字,而在于怎样理解课程方案提出的“探索大单元教学”,以及大单元教学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笔者认为,虽然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提出了“探索大单元教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各门学科都必须实施大单元教学,不能对其表示怀疑。
既然是“探索”,就要弄清“探索”的含义。所谓“探索”,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意为“多方寻求答案,解决疑问”。它是指对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的事物进行研究和探讨,如探索宇宙奥秘。就拿大单元教学来说,究竟怎样施行,至今尚无可供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尤其是语文教学),而是处在“寻求答案”的阶段。既然如此,就不应视之为课改的方向,大张旗鼓地推行。实际上,某些推行大单元教学的专家学者并未拿出已见成效的范例;而是从理论到理论,空谈大道理。所谓大单元教学不过是一个舶来品,源自美国教育家莫里逊在1931年提出的“莫里逊计划”,该计划主张将教材或活动划分为完整单元实施教学,强调学生通过实践活动获取系统化知识(也有人认为大单元教学源自杜威的弟子克伯屈提出的“设计教学法”)。它只是一种主张和构想,并非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并未广泛运用于各科教学。正因为如此,新修订的语文课程标准没有出现“大单元”三个字,课程方案虽然提出了“探索大单元教学”,但并未大力倡导。而某些专家学者却刻意抬高其地位,把“探索”演变为导向,甚至把它吹得天花乱坠,似乎不实行大单元教学就是守旧,就会落后于形势。这实际上是对“探索大单元教学”的曲解,是对课程方案的误读。
二、大单元: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
要“探索大单元教学”,就必须了解:什么是“大单元”?它和通常所说的“单元”有何联系和区别?怎样确定“大单元”?但无论是新修订的课程方案,还是极力推行大单元教学的专家学者,都未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们只是见到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修订组组长崔允漷教授所作的一番语意不明的表述。他在中国教育学会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心“首届全国课堂教学研讨会”上这样解释“大单元”:“这里所说的单元是一种学习单位,一个单元就是一个学习事件、一个完整的学习故事,因此,一个单元就是一个微课程。”这显然不是“大单元”的定义,而且这句话明显不符合逻辑。“大单元”和“学习单位”“学习事件”“学习故事”“微课程”本是不同的概念,怎能将它们划上等号混为一谈?老实说,我们无法从中了解到什么是“大单元”,这样的解释根本没有实际意义。此外,崔教授所作的以下判断也经不起推敲:“一个单元就是一个学习事件、一个完整的学习故事”。所谓“事件”,是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见《现代汉语词典》),学习本是平常的活动,怎会发生“不平常的大事情”?而“大单元”作为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又怎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学习故事”?
这样的“大单元”未免太玄妙,不知崔教授能否提供典型的案例,让我们开开眼界。
“大单元”这一概念的模糊不清,必然导致大单元教学理论也陷入混乱。让我们再看看崔教授对大单元教学的阐释,他在《学科核心素养呼唤大单元教学设计》(《上海教育科研》2019年第4期卷首语)中谈到:“大单元教学蕴含着三层深刻内涵:首先,它倡导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大概念、大任务、大观念与大问题的设计,来提升教师的教学格局;其次,针对教师们往往只关注知识、技能和分数,而忽视学生能力、品格和观念培养的问题,大单元教学强调全面育人的理念;最后,从时间维度来看,大单元教学有助于教师正确理解时间与学习的关系,确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窃以为,崔教授这段话与大单元教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要推行大单元教学,就应该让教师们知道大单元教学和通常实施的单元教学有何区别,如何确定其教学内容和运用什么教学方法。但崔教授对此却只字不提,而是从“理念”到“理念”。其“三层深刻内涵”所提到的“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强调全面育人”“以学习者为中心”本就是课程改革的要求,也是通常实施单元教学所遵循的原则,这段话不过是通过组合,把它贴上了一个“大单元教学”的标签。所谓“三层深刻内涵”也并非逻辑意义上的内涵(逻辑上的内涵必须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几项大而空的要求,且很难付诸实践。例如:怎样在“大单元”内进行“大概念、大任务、大观念与大问题的设计”(须知概念和观念都不是“设计”出来的)?“全面育人”之“全面”如何体现?时间与学习的关系应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泛化的且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容把“大单元”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究竟怎样实施,却不得而知。
正因为“大单元”是一个模糊概念,大单元教学也缺乏明确的界定,所以一线教师都感到摸不着头脑。不仅如此,“大概念”“大情境”“大任务”“大问题”“大项目”等无不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关于“大概念”,笔者在已发表的文章中对其翻译上的错误和逻辑上的漏洞进行过评析,故不赘述)。以“大任务”为例,它和“学习任务群”中的“任务”是什么关系?二者有何区别?“大任务”是从属于“学习任务群”还是另立门户?“大任务”应该怎样确定?由谁来确定?这些问题均没有明确的答案,教师根本无法操作。总之,用这些“大”而无当、模糊不清的概念指导语文教学,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三、“大单元”和现有的单元:是取代还是并存?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语文教材是按单元编排的,教师也基本上据此实施单元教学。各单元以人文主题组元为基础,按照一定的序列,安排听说读写的训练。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其单篇课文并非完全独立,而是与知识和能力相关联。虽然这种编排体系还存在不少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从整体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拿美国语文教材来说,也是采用这样的体例,整套教材按不同的主题编排,凸显出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开放性和综合性,而且十分注重语文能力的训练,具有明确的目标要求和很强的操作性。这并不是说其教材已完美无缺,但至少说明现行教材的单元体系自有存在的理由,不宜彻底推翻。
然而,“大单元”却要另立标准,重新建立语文学科的单元体系。这样的“探索”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谁能承担如此重任?某些推行大单元教学的专家由于自身缺乏语文教学的经历,只能是纸上谈兵;一线教师不仅受水平的限制,而且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按照有关专家的阐述,大单元教学的设计仍要以教材中的篇目为基础,那为什么语文教材不按大单元教学的要求进行修订,却把这项“系统工程”交给一线教师来完成?由于对大单元教学的界定模糊不清,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说法,因此没有人真正将大单元教学运用于实践。而从目前推出的一些名为“大单元教学”的案例来看,不过是根据个人的理解组合(实为拼凑)而成。这种各行其是的“探索”,很难形成共识,如同俗话所说,乃“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笔者认为,在大单元教学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下,将其作为课改的导向,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那些推行者只不过动动嘴和笔,自己无须或不敢做出示范)。面对这股“大”潮的冲击,语文教学已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到底是按照“大单元”的要求重组教材中的篇目或重建单元教学体系,以取代现有的单元;还是进行部分改造,即“大单元”和现有的单元(“小单元”)二者并存?如果用“大单元”取代现有的单元,就必须全方位地调整语文教材的单元体系,这显然不切实际,也没有人可以胜任;如果二者并存,则不可避免地相互冲突,使语文教材或教学的体系变得不伦不类。正因为大单元教学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可行的方案,所以语文教师只能各自为阵。这样一来,所谓“大单元教学”便成了“盲人骑瞎马”。它不仅造成了广大教师的思想混乱,也使大单元教学的“探索”陷入了困境。
四、外来理论只宜借鉴,不应照搬
和任何改革一样,课程改革首先是思想的变革和观念的更新。这种更新包括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教育理论(如建构主义、合作学习理论、多元智能理论、非指导性教学理论等),但外来理论无论多么先进,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绝不能菁芜不分地全盘吸收。就拿“大概念”(实为“大观念”)“大单元”来说,在国外的教育理论中不过是“一家之言”,并未被广泛吸收和应用,也未使国外教育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国内某些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却如获至宝,将其奉为圭臬,并把诞生于上世纪之初的“大概念”“大单元”当作我国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窃以为,这种生搬硬套的“拿来”和牵强附会的“挂钩”,是妄自菲薄的表现。
语文教育在我们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语文课改必须立足于本土,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母语教育的先进经验。语文教育当然应该与时俱进,改革那些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教学方法,但这种改革不是对传统教育的颠覆,以未经检验的做法取而代之,不能违背语文教学本应遵循的基本规律。语文是一门厚积薄发的学科,所谓“厚积”,就是多读多写(其中包括多思),此乃语文教学之“本”。关于多读,不单指课内阅读,还包括课外阅读,语文课程标准也强调要“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没有广泛的阅读,学生不可能有丰富的积累,语文素养也不可能真正提高。语文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必须建立在促进学生多读多写、爱读爱写的基础之上;而不应忘了语文教学之“本”,把扎扎实实的读与写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大单元教学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连贯性的教学方法,与传统的以零碎的知识点或技能点为主线的教学相比,它更加注重知识之间的联系与整合。应该说,这对于那些具有明晰的知识体系的学科不无指导意义。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如数理化)相比,具有诸多不同的特点,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语文没有必须严格遵循的学习顺序,也没有多少类似于数理化中的公式、定理等非学不可且环环相扣(不学就不能进入下一步)的显性知识,不存在非读不可的文章。语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其知识的习得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很难像学习数理化的公式、定理那样立竿见影地掌握和运用;而重在感悟和潜移默化。因此,试图把它“整合”成严密的知识和能力体系是不切实际的(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有用的知识和必须具备的能力),也违背了语文学习的基本规律。语文教学必须求实务本,不可为创新而创新,弄出一些“大”而不当和华而不实的新套路。温儒敏先生在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语文教育基本问题”专家座谈会上也谈到,要防止现在已经出现的形式主义、假大空的倾向,不宜笼统提倡大语文、大单元、大情景教学。作为统编版语文教材的总主编,温先生对当前语文教学中出现的盲目求“大”的现象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对于莘莘学子而言,语文学习本应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他们可以在广泛的阅读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在贴近生活的写作中享受运用语言文字的乐趣。如果罔顾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抛弃前人积累的宝贵经验,把西方的教育理论简单地“舶来”,并生造出一些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把本不复杂的语文教学弄得玄妙莫测,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它必然使广大教师无所适从,给学生造成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并将语文课改引向歧途。



 扫码安装网站APP(Android版)
扫码安装网站APP(Android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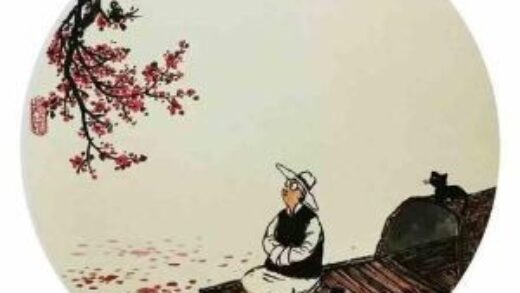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