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众号:Glimmer译站 作者:GJ436b

关键词:生物学;思想史;科学史
细思之下,微小如活细胞之物竟有着如此复杂的行为,着实令人惊叹。以单细胞生物变形虫为例,变形虫能感知环境、四处移动、获取食物、维持自身结构并繁殖后代。细胞为什么能够进行这些活动?生物学教科书会告诉你,构成从人类到变形虫等一系列生物的每个真核细胞,其内部都有一个叫“细胞核”的结构作为“控制中心”,细胞核内的基因持有细胞运作所需的“信息”,而细胞核又在于一种叫“细胞质”的胶状液体中,细胞质包含细胞器——即细胞内的“小器官”,这些细胞器根据基因提供的“指令”执行特定任务。
简言之,教科书描绘了一幅细胞“流水线”图景:基因发出指令制造蛋白质,再由蛋白质完成身体日常运作。这种对细胞的教科书式描述,几乎逐字对应着一种社会制度。细胞质及其细胞器根据基因“指令”执行分子“制造”、“包装”和“运输”工作的图景,可怕地呼应着社会等级——高管下令,劳苦大众进行体力劳动。唯一的问题在于,细胞并非“工厂”,细胞没有“控制中心”,正如女性主义学者艾米莉·马丁(Emily Martin)所指出的,中央集权控制的假设歪曲了我们对细胞的理解。
大量生物学研究表明,“控制”和“信息”并不局限于“顶端”,而是遍布整个细胞,细胞器并非仅形成线性的“流水线”,而是以复杂方式相互作用着,细胞也并非如“工厂”隐喻所暗示的那样,痴迷于具有经济意义的“制造”工作,相反,细胞的许多工作可看作是自我维持以及“关照”其他细胞。
那么,为何标准教科书仍将细胞描绘成一种等级结构?为何要借助中央权威来解释每个细胞的功能?其意象为何如此充满工业色彩?
或许这种细胞观在我们听来“显然”且自然,是因为其与我们的阶层社会及中央集权制太过相似,但执着于将此类隐喻作为科学的替身,其问题在于:关于细胞“应如何”运作的假设,会阻碍我们理解细胞“实际如何”运作。更甚的是,当科学将社会等级投射到细胞上时,也强化了社会等级“天然合理”的观念。
将社会等级投射于自然之上往往并非有意为之,就细胞而言,这种隐喻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一方面,当生物学家开始研究细胞内的化学作用时,他们发现“工厂”隐喻相当有用,例如,19世纪德国生物学家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Virchow)曾写道:“淀粉在动植物体内的转化过程,与在工厂中别无二致。”随着研究者对细胞器的探究——从内质网制造蛋白质,到线粒体产生能量——“工厂”隐喻引导了科学家谈论这些细胞器的方式。
另一部分历史则涉及生物学的不同领域——科学家试图弄清微小细胞如何孕育出像我们这样的多细胞生物。一些人认为精子内包含一个雏形人(homunculus),一个已然成型的小型人体,另一些人则认为生物母体为胚胎提供全部物质基础,而父体仅提供一种“生成力”(generative force)来促进卵子发育。直到科学家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受精过程,才发现父母双方各贡献一个细胞给下一代,但这两个细胞并不平等,与精子相比,卵子体积巨大(几乎是精子的一千万倍大)。
古老的谜题似乎得以解决:父系对后代的贡献远少于母系,当然,除非真正重要的是精子和卵子中共有的某个微小成分,19世纪末的显微镜观察显示,当精子和卵子在受精过程中融合时,它们的细胞核也一同融合,精子与卵子的细胞核大小相似。科学史家如汉斯·约格·莱茵伯格(Hans-Jörg Rheinberger)和斯塔凡·穆勒·威勒(Staffan Müller-Wille)曾描述过早期研究者如何开始将卵子和精子融合产生的细胞核视为遗传信息的源头,物理学家兼女性主义学者伊芙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指出,20世纪的生物学研究更聚焦于细胞核,却轻视了卵子其余部分的作用。
对细胞核及其所含物(基因作为“信息”)的推崇,至今仍在科学话语中占主导地位,与此一致,“细胞即工厂”的隐喻至今仍占据主导。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是客观且价值中立的,但科学哲学家指出,价值观能影响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构建的假说以及解读结果的方式,女性主义科学研究领域尤其对细胞核在遗传方面的唯一角色提出了质疑。
当然,细胞核确实贡献部分遗传特性,我们已深入了解其细节,但细胞核仅是遗传物质的微小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甚至不曾在卵细胞中寻找遗传信息——如果我们从不将那种信息描述为遗传性的——我们会持续传播一种观念:生物遗传仅局限于细胞核。
多年来,与女性主义学者并行,对旧思维的挑战日益增多。我们现在知道,其他几种遗传信息遍布整个细胞,例如,研究胚胎如何从单细胞发育而来的发育生物学家已证明,卵细胞细胞质中各种分子的空间布局有助于确定生长生物体的头尾方位、背腹面如何差异化发育等,卵细胞的细胞质并非仅仅“滋养”细胞核,它还包含着世代传承的编码信息。
如今,像马塞洛·巴别里(Marcello Barbieri)这样的生物哲学家正试图理解“信息”一词在细胞语境中的真正含义,在生物学中,遗传密码似乎是我们唯一听闻的密码,但这真的公平吗?——或者,这仅仅是科学家所处的等级社会所衍生的一种偏见?
巴别里在其著作《有机密码》(The Organic Codes)(2009)中,论述了在细胞核“遗传密码”作为至高无上之物被“发现”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预设,首先是“基因中编码的信息指导蛋白质构建”这一观念,也正是在此预言之后,实验才发现DNA并将其概念化为“遗传密码”。
细胞器间精妙的相互作用,直接挑战了工厂模式自上而下的秩序观
巴别里称此发现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由于科学家从未对细胞质中的“密码”做过类似假设,他们也就没有同样迫切地去寻找它们。我们都知道基因包含制造蛋白质的模板,但是,基因并不包含制造蛋白质所需的全部信息,基因仅指定了一维的蛋白质链,而对蛋白质功能至关重要的三维结构,则是由细胞环境决定的。此外,蛋白质的行为方式也因其在细胞质中的位置而异,单凭遗传“信息”,远不足以让细胞运作。
研究细胞器如何相互作用的生物学家提供了更多关于细胞质中信息的洞见。我们现在知道,教科书构建的那种线性“流水线”根本上忽视了细胞器的众多功能,也未能体现细胞器相互“对话”并影响彼此行为的多种方式。细胞器间精妙的相互作用,实际上直接挑战了中央集权式工厂所暗示的那种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秩序观念,这座“工厂”里的各个“部门”似乎在相互沟通、彼此发出指令,而并未让“总部”知情。
细胞质中所有这些编码信息让我们不禁要问:旨在呈现当今标准及公认知识的现代教科书,为何仍将细胞描绘为等级结构?科学记者在讨论生命如何发展与进化时,为何仍只提及细胞核中基因的密码与程序?
我认为,这种中央集权观的持久影响力,源于其与人类社会秩序的共鸣。在父权社会中,细胞核提供指令、细胞质执行“滋养”劳作的模式听起来很“自然”甚至“显然”,在阶层社会中,中央细胞核命令其“下属”细胞质实际执行任务的模式也显得不言自明。
拥有不同社会背景的科学家,是否会提出不同的细胞观?
有可能。看看生物学家E·E·贾斯特(E E Just)是如何看待细胞的:贾斯特曾研究过早期卵细胞的外围细胞质,在其著作《细胞表面生物学》(The Biology of the Cell Surface)(1939)中,他认为细胞质能够“自我调节与自我分化”,反对那种将细胞质降格为仅仅执行“滋养”劳作模式的主流发育观,贾斯特也是一位生活在20世纪初美国的黑人科学家。

1914年的贾斯特,《细胞表面生物学》的作者。照片来自芝加哥大学。
发育生物学家斯科特·吉尔伯特(Scott Gilbert)曾结合贾斯特的社会地位分析其科学观点,标准的发育观认为,发育指令位于中央基因中,与此相反,贾斯特认为细胞质具有“发育”的“潜能”,而细胞核的功能是为其路径增添或移除“障碍”。
贾斯特眼中的细胞质,无需细胞核的明确指令即可运作,细胞质能够自我管理并发育,只要当权者能移除其道路上的“障碍”。历史上,大多数科学家是男性、上层阶级,且属于主导种姓和种族,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很可能助长了他们对以下观念的认同:一个持续发号施令的细胞核,同时将实际工作中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视为理所当然。诺贝尔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将基因描述为“高管层”(executive suite),将细胞质描述为“工厂车间”(factory floor),高管层似乎更有价值、更配得高额报酬,而车间里劳苦的大众则似乎仅仅是在执行指令,其丰富的显性与隐性知识及技能受到了低估。
你或许会争辩说,“细胞即工厂”仅仅是个隐喻,你可能会说,科学隐喻应基于其有用程度来评判,没有隐喻是完美的。“细胞即工厂”的隐喻无疑在引导细胞生物学研究轨迹方面非常有用,我完全同意这些观点,我想指出的,是其他隐喻的缺失。正因为没有隐喻是完美的,我们才应运用多种隐喻来解释细胞的各个方面,不幸的是,教科书里无处不在的中央集权式等级隐喻,常常是描述细胞内部运作的唯一隐喻。
在此,我提出另一种隐喻:细胞核或许可以是一个“协作性笔记簿”(collaborative notebook),细胞保存着这本笔记簿,所有细胞组成部分都用它来追踪自身活动并协助维持细胞,细胞在笔记本上“书写”,在“页边空白处”注释,并“参考”自己的笔记,细胞器能感知彼此需求并相互“照料”。“工厂”隐喻将控制权和信息归因于细胞核,而“笔记簿”隐喻则展现了细胞自身的能动性,“工厂”隐喻让细胞看似执着于“生产”,而“笔记簿”隐喻则凸显了细胞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助性以及维持细胞存续的劳动。
为何我们在科学话语中找不到此类隐喻?为何谈论细胞器相互“照料”显得过于拟人化,而谈论基因“号令”其“下属”时却不会?这种选择性的拟人化,是否会通过公认的科学隐喻,强化中央集权控制的意识形态?若果真如此,除非我们反思自身的想当然,否则将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细胞的运作方式,若想理解细胞这种非计划型的结构,我们必须改变观察世界的“透镜”。
除细胞运作原理外,这种讨论对科学具有更广泛的启示。细胞并非唯一用于中央集权隐喻描述的自然系统,我们认定昆虫社会拥有“女王”及字面意义上的“种姓”结构,也认定存在“阿尔法”(alpha)雄性灵长类“领导”群体并维持其“后宫”(harems)。
当价值观干预科学时,对真理与精确性的追求便面临风险
我们之所以觉得中央集权模式无处不在,未必因为它真的无处不在,而只是因为我们透过特定的“透镜”观察世界。当科学叙事凭借科学权威,将社会等级结构投射于自然时,同时也强化了这种等级结构,令其显得“天然合理”。从细胞到动物社群的中央集权模型都暗示着自然界万物皆为中心化,且中心化行之有效。关于自然的“真理”受我们价值观影响,而此“真理”又能反过来强化社会价值观。
你或会问,这有何紧要?毕竟,无论自然如何,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理应与之区分,暴力存在于自然,但这不使其“正当”。
然而,科学史学者洛兰·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在《反自然》(Against Nature)(2019)中写道,关于何谓“自然”的论述始终承载着道德重量,自然或许并不决定道德,但可施加影响,另一重要方面,当然是对准确描绘自然的期望,若将社会不平等投射于细胞会扭曲我们对细胞的理解,我们就应警惕这种投射——因为理解细胞对生命科学进步和人类健康至关重要。
科学如何概念化细胞,亦让我们洞察自身对科学客观性的思考。我们常认为,当价值观干预科学时,对真理与精确性的追求便面临风险,科学家理应将其价值观与信念置于实验室门外,但女性主义科学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做出优秀科学成果未必需要隔离价值观,但否认其影响反而会损害科学工作的质量,相较于否认,反思价值观与偏见能助研究者避开陷阱,自我反思能助科学家研究价值观如何塑造其科学,并构思更佳实验方案以预防其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
科学无疑是一项人类事业。女性主义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将科学描述为一种局部视角间(partial perspectives)的对话,每个个体皆从其所处地位获得独特视角,正如贾斯特的科学所示,拥有不同生活经验的人或具不同视角,并提出不同问题。诚然,科学家背景与其工作间的联系并非总是如此直接,但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仍可成为一个影响其工作的因素。我们常说,科学具备自我纠错能力,我们认为科学会在新信息出现时改变其观点,但新信息并非凭空产生,亦非仅源自新技术,当持不同视角者透过不同透镜审视同一数据时,新信息亦得以产生。尽管从公平性角度看,多样性与代表性本身至关重要,但多元视角最能惠及科学,客观性并非个体的负担,而是集体的责任。
若我们无法构想一个没有强制性等级结构的细胞(我们这类生物体的基本单元),我们将永远难以充分理解大自然的复杂性,若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中央集权的社会,我们将难以理解或赋权于被压迫者,除非我们反思自身假设,否则我们的科学将布满地雷,永远难以解开生命的所有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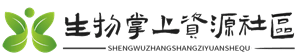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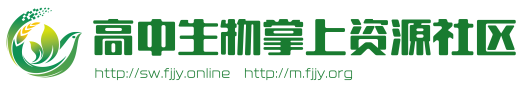
 扫码安装网站APP(Android版)
扫码安装网站APP(Android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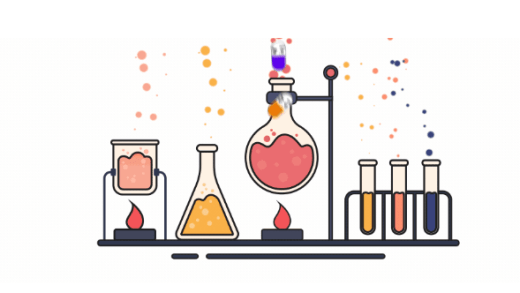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