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众号:柳浪文英 作者:柳夕浪

有人说我们对教学的理解要么是错误的,要么过于粗糙。现实似乎在验证着这一说法。好的教学到底什么样?
近来微信圈流传着学生跟着智能体学习外语单词的短视频,称不用老师教就学了几千个单词。同样的现象大量发生在学校课堂上:学生跟着老师读课本、做练习。“讲授和练习”占据了课堂上80%以上的时间。
这种储蓄罐式的教学背后的理念显然是有问题的。

而某些专家推荐的建构主义学习模型、发现教学法等因过于乐观或者过于理想化而又存在争议:
对知识的理解并非像杜威或皮亚杰假设的那样,自动地以“反省抽象”的方式实现。如同学习游泳,你只是把学生抛到水池,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有风险。
1 一个案例
安德烈·焦尔当和裴新宁合著的《变构模型》一书,提供了一个12—13岁学生关于呼吸概念教学的例子。

教学之前首先通过半开放问卷和访谈,了解学生的原初观念,涉及以下问题:
| 1.对你来说,呼吸意味着什么? 2.人是怎么呼吸的? 3.肺有什么功能?在肺里的空气变成了什么? 4.血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5.氧气发挥着什么的作用?二氧化碳的作用又是什么? …… |
调研发现,学生认为呼吸是由肺进行的,只有10%的学生认为呼吸的空气不局限于肺部,而且与心脏和血液有关。许多学生认为,氧气是“进入的空气”,是“纯净”的;二氧化碳是“出去的空气”,是“污染物”“会引发窒息”。有的学生认为,空气的存在是有形的,看不到的东西就不存在,在水中,空气只能以气泡的形式存在,等等。
从中不难看出,学生的原初认识与关于呼吸的科学概念是有距离、有冲突的。
从学习角度看,这些原初观念就是学习者认识世界的基点和工具,每个学习者都是从自己的原初观念出发,去面对新情况、新任务。同时它又是阻碍其理解的意向和智力“牢笼”。在大多数情况下,学习者倾向于排斥新的东西,排斥那些不能引起共鸣的新知识,如此学习难以真正发生。
接着,查明学习的障碍。
分析发现学生之所以这样看待呼吸现象,是因为缺乏相关的物理化学概念或者被一些错误定义的物理化学概念所左右。如不知道空气的组成;把气体、空气和氧气混为一谈;只是记住了氧气和二氧化碳等名词,并不理解它门,等等。他们的参照框架是一个机械的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呼吸是一个限于肺部的现象,它被看作是一个安全的黑匣子。而这一切又与学生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日常生活经历有关。
进一步分析学生原初概念背后的假设: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具体原因是什么?
从中可以看出,关于呼吸的科学概念建立既要与相关概念建立意义联结,还要求改变其背后的认知框架。
然后,选择相应的教学策略,进行教学干预。
策略一:教师仅让学生阐明自己的理解,并不提供信息。结果,学生通过自学、交流,认识到:
- 生命需要氧气。没有空气,动物会死亡;没有氧气,动物也会死亡。这是为什么?
- 一些动物用肺呼吸,另一些动物同样用肺呼吸,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呼吸是怎么进行的。
- 水中的动物会呼吸,但是怎么进行的?它们也有些运动,这是为什么?
……
在完全让学生自主学习的情况下,学生的认识很难说发生了质的变化,只是生发出更多的疑问。
策略二:教师让学生阐明自己的认识,并讲述自己认为必要的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结果发现,学生学习所达到的认知水平低于策略一。教师的直接讲授,事先提供的那些关于呼吸的知识妨碍了学生的思维,学生没有了思考空间。

策略三:教师让学生阐明自己的理解,并根据学生小组遇到的问题,逐步引入相关实验,讨论有关问题。
如学生认为“肺是必须有的”。
教师:怎么证明它们是必须的?
学生:我们可以把肺去除,然后看结果。
实际教学中该实验未进行,教师提供了关于切除狗的肺的实验信息,并组织学生对一条鱼进行解剖,出示解剖图。
学生:也许一些动物没有肺也可以呼吸。不过它们真的在呼吸吗?学生在想象中将不同的动物放在密封瓶里,并进行新的实验:将不同动物放在装有石灰水的小密封瓶里。基于实验,学生有了新的认识:所有动物都会呼吸,甚至包括那些看不到它们鼓气的动物。没有肺的动物也会呼吸。
从实施策略三的教学实践中,学生认识到:
- 用于呼吸的是水中或空气中的氧气。
- 氧气进入血液中,然后流经各个器官,在那里氧气得以进入,而二氧化碳被排出。
- 关于植物,我不太明白。它们晚上呼吸,白天却相反。……
学生开始接近科学概念,对概念的表达形式也在不断丰富。这些概念也不再是静态的名词,而转化为实践性知识(动词),用来整合其他知识。
当然,呼吸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特别是尚未涉及到“能量”这个基本概念,肺和心脏的关系等。如让学生对呼吸运动的次数和心跳次数进行计算;还可以制造一种情绪,以便观察心跳加速,而呼吸节奏却没有改变,目的是与学生原初认识形成冲突,进一步认识到呼吸并不止于肺,它还牵连血液和细胞本身(红细胞对氧气的输送)等。
2 三点认识
第一,学习不仅是一个意义建构过程,还是原有观念(先验假设、前概念)的解构过程
人脑神经细胞承载着在几百万年进化中积淀下来的信息,储存了数以千计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内在模型,就像一台机器,内含了足够多的回路装置和先验假设空间。如婴儿知道物体只有在被推动时才会移动,人和物体不一样,已经具有对物理世界的直觉,会对意料之外的结果感到诧异,只是不能像成人年那样表达出来(学习其实很难完全撇开遗传因素)。

先验假设与后天经验一拍即合,每个人凭借此快速适应周围环境变化,每遇新情况、新问题,倾向于在已有的认知框架内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与之相悖的证据既看不到,也听不进去。
真正的学习不是新信息的简单添加,对新知的掌握很少以自动的、直接的方式实现,必须放弃习以为常的东西,打破原有的心智结构,这便是解构。

解构和建构是同一发展进程的两个侧面,它意味着在相互矛盾、相互干扰中的心智结构中重组知识,强化与特定的情境脉络的联系,伴随着假设引导下的推理、论证,对没有对原初不当观念的解构和新的意义建构。
福尔摩斯在一部小说中写到:
“还有其他什么地方需要我注意的吗?”伦敦市警察厅的格雷戈里警官问道。
福尔摩斯:“我很好奇当晚那只狗干了什么?”
格雷戈里:“那只狗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做。”
福尔摩斯:“那正是有趣的地方。”

福尔摩斯推断:如果那只狗看到了陌生人,那它一定会叫。由于它没有叫,犯罪者一定是狗的熟人。
那些跟着智能体背外语单词的学生如同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人把《新华字典》背下来一样,脱离了语境,什么假设、推理、论证、说明等高级认知活动不会发生,也谈不上字词的理解和运用。
试问:今天,把《新华字典》装在头脑里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教学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与学习者原初的看似适用其实僵化的观念对质。

每个学习者都有一套自己的问题、想法、反应倾向、推理方式等,试图让他们主动放弃不符合情境的认知和行为方式、自动建构新的意义,通常是不现实的。
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解构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职业场景中调用学校知识始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将日常生活知识迁移到学校情境在也同样不易”。
为此,我对“学为中心”持慎重态度,因为它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教学虚无主义:一种只关注学而不关注教的倾向,一种以学习科学替代教学论的现象。

上例把教学称为“干预”,一种有意引出与学生原初观念不同的事实、数据等,不断拓展认知视野,以改变学习者思维和行动轨迹的尝试,它召唤着学习者看到和思考看似熟悉实为陌生的生命世界,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构建新的认知框架,涉及到科学概念内涵、科学研究过程以及科学价值的捍卫、教学伦理等诸方面,成为教学活动的重心。
教学活动常常低估了原初观念的抵抗力,满足于一般性的讲授或学生的自主探究都可能有问题。我希望学习能变得容易些,但事实上学习是困难的,它是观念的搏斗,有起伏,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并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陪伴”那么简单。
如同让一个从未见过海的人对海和湖进行比较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他的头脑里,大湖就是海。

第三.教学的发生以学与教彼此间被理解、可预见(可见课堂)为前提的
人类学家向被试呈现这样一个情境:
甲有一个球,她把球放在椅子的垫子下,然后离开了。当她离开后,乙把球从垫子下拿出来,放到另一间房子的柜子里。后来,甲回来了。这时问被试:甲会认为球在哪里呢?
一直到四岁之前,大多数孩子会本能地说:甲会认为球在柜子里。
这个年龄的孩子无法区分自己和他人对世界的认知。

但到了四岁半以后,孩子的理解能力会有一个飞跃,会说:甲认为球在垫子下面,但我知道不在那里。这意味着孩子能够认识到其他人对世界的想法与自己不一样,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是错误的。
人类学家称这时候的孩子有了心理理解能力,一种将心比心、感同身受的能力(哲学家称为“意向性”,日常生活中叫“读心”)。它与事件的前因后果关系不大,而集中表现为与自身思想状态相关的反省性,意识到自己脑力子里的内容,相信那边灌木丛中藏着一个捕食者,相信自己脑力里的想法,并推断其他生物体的想法可能与自己不同。如上例中甲相信乙认为球在垫子下面。
心理理解能力是人类特有的显著而重要的心理特征,是一切教学活动发生的前提条件。
上例中,教师通过问卷和座谈了解到学生的原初观念及背后的假设,从学生的视角看课堂,基于学生言行推断他的思维方式,理解正在发生的学习,特别是诊断学生的认知误区是如何发生的,才有了课堂上与僵化观念的对质;与此同时,如果学生能站在他人(教师或同学)的角度,注意到他人的不同看法,理解他人为什么这么想、这么做,如此才有了双向开放,彼此向对方打开,有了反馈的接纳,有了“视界融合”,有了“可见的课堂”。你必须让对方看见自己,进而你才能看见对方,有了彼此间的相遇相识和改变。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的学习有潜伏期,今天的教学也许在10、20年之后才会有期待的教育效应发生,也就是说它并非像拉锯那样,往来立等可见。
研究发现,“教师对课堂上80%的事闭目塞听”,对课堂上发生的一切不能及时察觉,更谈不上诊断分析,“大约5%到10%的教师会将错误的答案作为讨论的跳板,以深入了解错误是如何发生的”。
如何让教学成为在当下被描述和被理解的可见的现象,能够从一生的角度看当下的课堂活动哪些重要、哪些无关紧要,创造“可见的课堂”“智慧的课堂”呢?
这或许是教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扫码安装网站APP(Android版)
扫码安装网站APP(Android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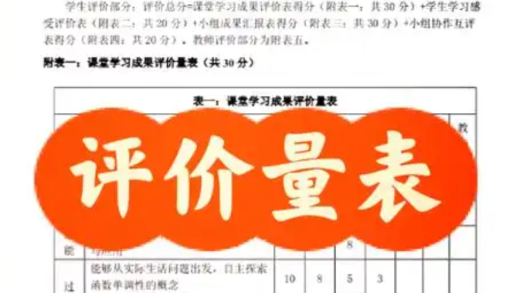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