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怡(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中学)
傅建利(杭州市富阳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 针对梅塞尔森-斯塔尔的DNA半保留复制实验,围绕标记物的选择、标记对象的选择、实验方法的创设和实验步骤的程序性设计,以及高中生物学教材中实验的示意图所呈现5个方面的疑难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 DNA半保留复制 梅塞尔森-斯塔尔 高中生物学
1958年,梅塞尔森(Matthew Stanley Meselson)和斯塔尔(Frank Stahl)做出了生物学史上最美的实验,证实了DNA半保留复制的猜想。该实验也是高中生物学教材中经典的实验之一,但师生常有以下困惑:实验为何选择无放射性的15N作标记物,而非放射性元素?实验为何选择大肠杆菌的DNA作标记对象,而非斯塔尔最为熟悉的噬菌体?实验为何选择密度梯度离心法对DNA进行纯化分离,而非差速离心法?实验为何从获得15N/15N-DNA做起,而非直接以14N/14N-DNA为模板做起?另外,对比全国不同版本高中生物学教材必修2中的实验图示发现,对于离心管中DNA条带的分布结果,部分版本的教材用双螺旋链状DNA的标记情况来解释,而非闭合环状,这是为何?本文就围绕这5个疑难问题,分别展开分析与讨论。
1 实验为何选择无放射性的15N作标记物,而非放射性元素
在20世纪50年代,大肠杆菌的“饮食偏好”引人关注,当葡萄糖和乳糖共存时,其代谢顺序总是先葡萄糖后乳糖。相关假说有两种:一是认为菌体早已合成代谢乳糖的酶前体,受诱导后才有活性;二是认为乳糖酶需重新合成。为辨别真伪,梅塞尔森提出了想法:用含氘的乳糖培养基饲养菌体,若酶是新合成的,便被会氘标记,其质量会比旧酶重。
受上述思路的启发,他联想到该方法也可探究DNA复制。故用无放射性元素来设计实验,是其自然发生的顺势思维。若一提到同位素,就和放射性绑定,实则是旁观者受到了早期经验主义的影响。如1952年赫尔希(Alfred Day Hershey)和蔡斯(Martha Chase)用32P和35S探究噬菌体的遗传物质。
在初期,该实验标记物不是15N,而是与胸腺嘧啶相似,但质量更大的5-溴尿嘧啶。由于被标记的与未被标记的DNA在离心管中分布得过开,同时负电性很强的溴原子能显著诱变DNA的AT对转为GC对,结果并不理想。其失败或许还与实验周期有关。为使DNA双链都带上标记,梅塞尔森和斯塔尔用标记物连续培养菌体15代,基因突变就被大量积累了。到1974年,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等人也以5-溴尿嘧啶为标记,但仅让植物根尖细胞繁殖了2代,或是短期内突变较少,结果反而较理想。
其实,无论使用何种元素,均有优缺点。无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法无辐射、无污染、无需防护,但灵敏度低、价格贵等;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法虽简单、较精确等,但辐射易造成伤害和污染。
2 实验为何选择大肠杆菌DNA作标记对象,而非噬菌体DNA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分子遗传学飞速发展,大肠杆菌和噬菌体早已成为被分子生物学家研究得最为透彻和使用得心应手的重要实验材料。自1945年起,德尔布吕克(Max Ludwig Henning Delbruck)、卢里亚(Salvador Edward Luria)和赫尔希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投入噬菌体研究阵营之中,斯塔尔便是其一,噬菌体的遗传学也成了他一生研究的主题。可见,把标记物标在噬菌体DNA上的初期思路,应该是斯塔尔利用了其研究的专长。此外,从生命系统的复杂程度上考虑,仅含蛋白质和DNA的噬菌体病毒比大肠杆菌简单得多,这也是噬菌体会成为首选材料的另一个原因。
在走过用5-溴尿嘧啶标记噬菌体DNA的弯路后,梅塞尔森和斯塔尔的实验思路便发生了一个很特殊,却又很成功的跳跃,不仅改用15N作为标记物,还改用大肠杆菌DNA作为标记对象。这是因为以大肠杆菌作实验材料,意外地避免了像噬菌体那样DNA分子间发生高频重组的情况。该情况也是引起初期实验结果混乱,较难以分析的重要原因。
3 为何选择密度梯度离心法对DNA进行纯化分离,而非差速离心法
依赖同位素在质量上的微小差异,来追踪DNA旧链在子代DNA中的去向与分布,这就要求离心技术的精密度足够高。差速离心通常不用于精细分离,待分离的颗粒在沉降系数差值上需足够大(一般为1到几个数量级),否则会效果不佳。梅塞尔森和斯塔尔通过先冷冻后离心的手段提取DNA,离心产生的机械剪切力和冷冻产生的冰晶易导致DNA断裂。因此,两人先后提取的3代DNA会长短不一。故从精细度和DNA长度上考虑,差速离心法并不适用。断裂的DNA虽在长度上发生变化,但其浮力密度不受影响,这就好似一根铁条不因其折断而改变密度。梅尔塞森设计的密度梯度离心法,凭借样品颗粒在浮力密度上的差异,在具有线性密度梯度的介质中离心,使颗粒悬浮在介质的不同区带。最重要的是,样品颗粒的质量大小和形状并不影响分离的效果。所以,密度梯度离心的有效使用,就不再受限于DNA长度一致的条件,DNA即便断裂也无妨。
4 为何从获得15N/15N-DNA做起(先15N后14N),而非以14N/14N-DNA模板做起(先14N后15N)
在不同版本的高中生物学教材中,该实验均是先用15N长期培养菌体以获得第0代15N/15N-DNA,再将菌体转到14N中培养第1、 2代DNA。最后,对这三代的DNA进行离心分析,证明了DNA的半保留复制。若修改程序,直接将含14N/14N-DNA的普通菌体,置于15N中连续培养2代。从理论上推测,这三代DNA应分别位于管中上部、中部、中部+下部,原结论貌似也成立。据《基因前传》一书的叙述,这两种程序均被设计与成功实施。在先14N后15N的程序中,实验可省略用15N标记亲代菌体以获得第0代15N/15N-DNA的环节。那为何中学教材只展示先15N后14N的程序,而不是另一种或两种都展示?这两位科学家的论文提供了答案:首先,全文并未提及先14N后15N的程序;其次,论文开篇直接先描述密度梯度离心法的设计思路,并尝试分离含有15N/15N-DNA与14N/14N-DNA的混合物,结果成功出现了2个条带,且密度差值为0.014 gm/cm3。该差值也为后续实验提供了对照,当14N/15N-DNA经高温解旋再离心,结果出现了两种新密度物质,且差值为0.015 gm/cm3,这与上述差值较接近。从而排除DNA复制的弥散型假说。可见,获取15N/15N-DNA,这一步程序是不能省的。
若从DNA甲基化的角度,分析两种程序,实验结果在区分度上有所不同。DNA具有半甲基化的特点,即亲链保持甲基化,新合成的链则未甲基化。这使旧链的密度本就比新链大。在先14N后15N的程序中,未甲基化的新链因15N的掺入,使浮力密度也增大,上述两种因素会相互抵消,减小了新旧链的密度差。这样,不同代的DNA在离心管中就难以被分开了。
5 为何是以双螺旋链状DNA的标记情况来解释条带分布结果,而非闭合环状
假说具有“真伪不对称性”的特质,即通过科学实验直接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较难,但通过科学实验推翻它却很容易。梅塞尔森和斯塔尔的实验结果虽使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的DNA双螺旋模型变得更为具体和可信,但两人刻意避免“股”“链”等字眼,而是用“亚基”(subunit)来陈述结论:每个亲本分子将两个亚基传递给后代分子。每个后代分子只接收一个完整的亲本亚基,还强调“亚基”尚不明确是单个多核苷酸链。这两位科学家仅从实验数据出发,避开了众多科学家默认的立场,客观地陈述自己也不确定本研究的DNA是双螺旋状的。直至1963年,凯恩斯(John Cairns)借助放射自显影技术才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大肠杆菌DNA是一个环状分子。所以,从时间上看,梅塞尔森和斯塔尔不可能会提前知道大肠杆菌DNA是一个环状闭合结构。
当大肠杆菌的环状DNA进一步相互盘绕,便构成超螺旋结构。在解旋时,超螺旋DNA是在局部解旋到一定程度后,再借助DNA拓扑异构酶断裂磷酸二酯键以松弛其构象,而非简单地直接分成2个单环。由于超螺旋结构的存在,也使得环状DNA具有很强的抗热变性。在解链实验中,加热只断氢键而不断磷酸二酯键,但异构酶发生了热变性,所以环状DNA并非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被分开。从今天来看,巧合也在这里,在提取时意外断裂的第1代14N/15N-DNA便在两人的预设中被加热解旋,并顺利地离心出了两个条带。
基于大肠杆菌DNA结构的发现时间、超螺旋结构和意外断裂三方面,教材中的图示仅以双螺旋链状DNA来解释结果,这点上是可被辩护的。
6 总结
综上所述,密度梯度离心为利用无放射性元素追踪DNA旧链的设计思路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托,跳脱性地调整标记物和标记对象也是成功的关键。在程序性设计上,原始论文未提及先14N后15N的程序,从DNA甲基化角度分析,该程序的实验结果在区分度上较低。在后续解链的实验中,获得15N/15N-DNA更是不可省。教材中的图示,仅以双螺旋链状DNA来解释结果,也是出于对环状DNA发生断裂的事实。
文献来源:罗怡,傅建利.梅塞尔森-斯塔尔DNA半保留复制实验的疑难探讨[J].生物学教学,2025,50(08):89-91.



 扫码安装网站APP(Android版)
扫码安装网站APP(Android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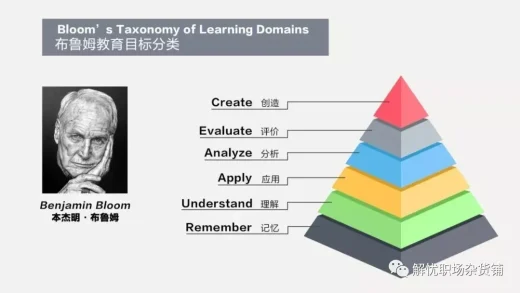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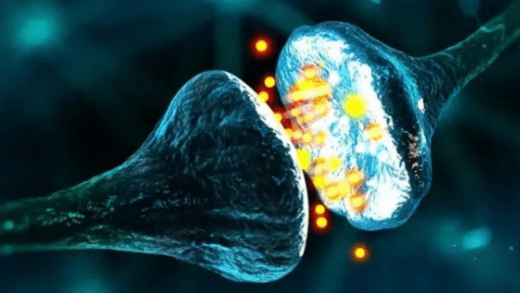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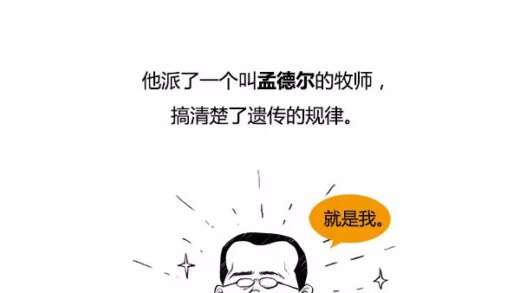
近期评论